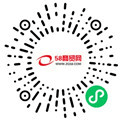騰訊財經(jīng)訊 據(jù)CNBC報道,當今社會,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早已不是新鮮話題,它們形態(tài)多變,而且隨處可見。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會被機器人取代。不過,美國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并不這么認為。Gartner預測,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的工作崗位很可能比它淘汰的工作崗位多。
澎湃新聞記者 胡志挺
財政部兩則通報再次引出地方債這頭“灰犀牛”。
12月22日,財政部對外通報,江蘇、貴州兩省近期查實多起地方政府違法違規(guī)舉債擔保問題,除責令限期整改,還對71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不同程度處分。
據(jù)新華社報道,盡管這并非財政部首次公開違法違規(guī)舉債擔保問題處理結果,但此次通報時機敏感,釋放出2018年黨中央、國務院將更大力度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要信號。
興業(yè)研究城投行業(yè)分析師程謙向澎湃新聞分析稱,財政部釋放這一信號,是對地方政府敲警鐘,有利于遏制地方政府舉債投資的沖動,從長遠來看有利于降低城投債的系統(tǒng)性風險。
就目前而言,高企的地方債務問題越發(fā)嚴峻。今年7月,中財辦官員明確將地方債務列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需要警惕的五頭“灰犀牛”之一。此外,審計署和財政部也多次通報地方政府違規(guī)舉債的情況。
興業(yè)研究宏觀團隊分析師何津津認為,從國外和國內(nèi)的角度來看,地方債務風險問題都是不得不處置的內(nèi)容了。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向澎湃新聞表示,在處置地方債問題時也不宜一刀切,畢竟各種債務形成原因不同。還是要在發(fā)展中解決問題,因為發(fā)展可以形成收入流。“要在適當提高債務限額的基礎上,從嚴管理。”
債務風險關鍵是借債沒有產(chǎn)出
債務問題的本質是投入與產(chǎn)出的關系。
上海對外經(jīng)貿(mào)大學金融學院講師鐘輝勇告訴澎湃新聞,如果借債有產(chǎn)出,其實并不擔心債務的償還,因為不存在違約的風險。現(xiàn)在大家擔心債務風險,其實關鍵是借債沒有產(chǎn)出,所以才會擔心債務引發(fā)的違約風險。
當下,地方政府的投資多偏向于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農(nóng)村水、 電、路等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項目,財務回報率普遍較低。鐘輝勇指出,現(xiàn)在地方債務問題一方面是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債務/GDP比例更高,但這些地區(qū)的債務償還能力卻更弱。如果這些地區(qū)的債務償還出現(xiàn)問題,最后壓力必然會轉移給中央政府。
程謙向澎湃新聞表示,從風險的角度看,可以說最大的問題是增速過快,而且地區(qū)差異很大,有些地區(qū)的隱性債務負擔已經(jīng)很嚴重了。另外地方政府舉債的時候都是手里的土地會升值,打算以賣地收入來還的,但是地價上漲難以持續(xù),如果房價下跌,政府的收入端也會受影響。
“根據(jù)融資平臺半年報和三季報估算,今年融資平臺有息債務增速大約在15%左右,比財政整體收入的增速要高。”程謙分析稱。
城投債仍在風險積累期,剛兌遲早會被打破
在何津津看來,最需要提防的一點是,在現(xiàn)在的政策導向下,明年城投債,作為“最后的信仰”,剛性兌付可能會被打破。何津津表示,這是市場角度來看最大的風險點。
所謂城投債,是指為地方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籌集資金,由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發(fā)行的債券,包括企業(yè)債、公司債、中期票據(jù)、短期融資券、非公開定向融資工具(PPN)等。
一般來說,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投資項目收益率偏低,但融資成本卻在不斷升高。如果某個地方融資平臺出現(xiàn)違約,這不僅會影響該融資平臺的后續(xù)融資,還會影響到整個財政系統(tǒng)融資的可持續(xù)性。基于此,地方政府為了滿足其融資平臺的融資需求,并降低其融資成本,就會以“剛性兌付”為保證。
對于地方融資平臺的“剛性兌付”的原因,鐘輝勇向澎湃新聞分析稱,首先是監(jiān)管部門的要求,即“絕不允許發(fā)生資本市場違約事件”。再者,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各種協(xié)調來保證本地融資的零違約,甚至在借債的時候,部分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會出具相應的“承諾函”,以此來保證債務的償還。此外,在中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地方政府不可能破產(chǎn),因而地方政府即便面臨違約時,中央政府也可能進行救助。
鐘輝勇表示,來自中央政府的財政專項轉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發(fā)行城投債的規(guī)模也越多,背后的原因就是地方對中央救助預期的存在而導致地方政府借債的道德風險問題。
程謙告訴澎湃新聞,近期城投債仍然處在風險積累的階段,但城投債的剛兌遲早是要打破的。一方面有部分區(qū)域的債務確實到了難以負擔的程度,另一方面不打破剛兌難以從根本上遏制城投債的無序擴張,難以完成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
其實早在2014年,國務院便發(fā)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43 號文”),其中規(guī)定地方政府不能再通過融資平臺舉債。換而言之,在此之后地方融資平臺的新增債務都不再屬于政府債務,地方政府不再承擔償還或者救助的責任。但在2015年之后,依然有不少地方政府繼續(xù)通過融資平臺借債。剛性兌付之下,債務違約風險被大大地忽視了。
“但是目前融資平臺流動性普遍都很好,在手現(xiàn)金很多,明年會不會打破剛兌還很難說,我認為至少不會大規(guī)模出現(xiàn)。”程謙說。
要在適當提高債務限額的基礎上,從嚴管理
就地方債務風險問題的監(jiān)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向澎湃新聞表示,一刀切肯定不行,畢竟各種債務形成原因不同。還是要在發(fā)展中解決問題,因為發(fā)展可以形成收入流。
鐘輝勇則認為,在具體措施上,應該把重點放在推動地方融資平臺的市場化轉型、放松地方政府債券融資規(guī)模限制并推進債券發(fā)行的市場化定價、加強金融監(jiān)管部門和財政部門之間協(xié)調這三個方面,最終實現(xiàn)金融體系資源配置效率的優(yōu)化。
楊志勇也表示,要在適當提高債務限額的基礎上,從嚴管理。
“但光靠監(jiān)管解決不了問題的根本,最后還需要讓地方政府完全自主地發(fā)行政府債券來解決融資的問題(不限額),一定要讓地方政府債券的定價市場化,這時債券利率才能反映地方政府的償還能力。”鐘輝勇指出,如果某個地區(qū)的政府違約風險高,就可以對地方政府要求更高的利率,這樣才能倒逼地方政府。